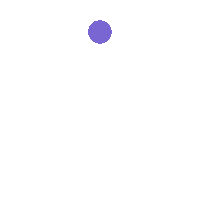報導重點摘要
- Metoo 運動自 5 月延燒至今,政治、藝文、教育、演藝圈等領域陸續有受害者揭露遭騷擾、侵犯的經歷,我們訪問了六個故事,她們曾在不同年紀、場域,被不同權力關係的人施以性暴力,也都嘗試尋求幫助。求救的過程遭遇了什麼?社會可以接住她們嗎?
- 法官坦承,部分性犯罪的案件可能只有被害人的證詞,找不到其他證據,最終獲不起訴或無罪,成為司法上的黑數。律師也指出,正因為性犯罪案件的證據太少,告訴人事發當下的情緒常會被當成關鍵的證據,「完美被害人」模板於焉出現,外界對性犯罪的受害者有著純潔的想像,其一舉一動常遭到檢討。
- 國外知名漫畫「我幫強暴犯做了早餐」的非典型受害者樣貌曾在司法界引起討論,加上近年愈來愈多的性別案件,律師發現愈來愈多法官跟檢察官在訊問時會盡量同理受害者。但仍有親身經歷司法程序的性暴力受害者認為,過程不僅繁瑣,也會遭受到檢察官或法官的不當提問,造成二次傷害。
- 律師也提到,就算性犯罪案件不成立,並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,往往只是找不到足夠的證據去支撐證詞,希望社會能以同理心接納被害人,而不是以判決結果來予以批判。
怡玲(化名)終於決定將自己的故事公開在社群平臺上。她去年被職場認識的人性侵未遂,從此人生多了一個找不到答案的問題:「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?」。一天天不斷爆出的 Metoo 故事喚起記憶,她花了好幾天才將曾經發生過的事書寫出來。
準備公開被侵犯的經驗讓怡玲很緊張,但她受不了了,一定要把文章發布出去,「我一發完就立刻把網路關掉,一直哭,我很害怕,非常害怕,一開始還不懂自己在怕什麼,後來諮商師跟我說,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會怎麼看待這件事,很怕外界的惡意。」
沒想到發完文之後,怡玲收到大量私訊,持續了好多天,每天都有很多曾受到侵犯的人傳來訊息:多數是陌生人,也有些認識但不熟的人,甚至還有朋友主動傾吐他們的故事,「我很震驚,再來也很捨不得,會覺得,天啊,真的是太多了。」
從任何地方到任何關係 性犯罪無所不在
怡玲的驚訝其來有自。從過去一年性犯罪相關案件的判決書中可以發現,任何人在任何場所都可能遭遇性暴力:可能在餐廳裡、公車上、馬路邊;可能是側身經過的陌生人、萍水相逢的超商店員、或是熟識已久的親友長輩。

在我們收集的資料中(不包含司法院判決書系統判定不公開的內容),被害人與加害人的關係以陌生人居多,犯罪模式大多是突襲觸摸身體部位。至於親屬、職場、社交、教育等雙方相識的關係中,案件數較少,但性侵害的比例較高。
不過,律師林家萱解釋,被陌生人騷擾,被害者會因為彼此的生活無交集,比較願意提申訴或刑事告訴,此類案件在法庭上的攻防也相對單純;然而熟人之間的性犯罪,會因為雙方存在情感、經濟或社會上的依附或信賴關係,使得被害者不敢揭露對方犯行,更別提進一步的提告,因此性犯罪的黑數很多。此外,熟人性犯罪也會因證據難取得,結局往往是不起訴或無罪。
諮商心理師陳湘妤就差點成為家內性侵的黑數。她從國小一年級遭到爸爸侵犯,直到國一時媽媽致電 113 專線詢問「老公會摸小孩的身體怎麼辦?」,事件才曝光。她說,當時 113 人員欲詢問細節,媽媽改口稱「沒有沒有」,好險對方機警,循線找到她就讀的學校,開啟後續的安置和司法程序。
長達近 8 年的時間,陳湘妤的爸爸先是用零用錢和禮物為餌,要求女兒和他接吻;接著藉故撫摸、舔拭她的胸部和私處,或是用下體磨蹭身體;等她年紀稍大,爸爸甚至會在孩子的零食裡摻入安眠藥。
「有一天我醒來,就發現褲子衣服全被脫掉,然後他在舔我下面。」陳湘妤表示,兩姊妹跟媽媽提過好幾次「爸爸晚上會偷進我們房間,他會摸我們」,但媽媽只說會處理,要孩子們不要說出去;等她開始出現第二性徵,媽媽才跟爸爸說:「她現在月經來了,你不要再這樣了,如果孩子懷孕怎麼辦?」
童年的回憶滿是憤怒、害怕和痛苦,在陳湘妤和姊姊成年後,兩人不經意談到過去的日子,姊姊跟她說曾在生活百貨看到門閂鎖,「就是那種可以鎖在木頭門上面,扣起來的鎖,姊姊說一個只要 30元。」
陳湘妤苦笑,媽媽曾經幫他們的房門換鎖,但她不小心弄丟鑰匙,最後被爸爸撿到,「從此我只要東西不見,都會非常焦慮,因為我一直覺得那是我的錯。而那時候其實只要一個 30 元的鎖,我就能保護自己。」
受害者依賴加害者 導致熟人性侵案難辦
陳湘妤說,媽媽曾告訴她,已經用盡全力在抵抗爸爸,「但她不知道,如果沒有這個男人,生活要怎麼過。」作為一名陸配,能在臺灣取得合法居留的資格,且擁有穩定的經濟支撐,都得仰賴她的丈夫,陳湘妤表示,當時一直以為父母終究會離婚,然而當事情揭發後,媽媽的態度仍堅定地和先生站在一起,這讓她花了很多的時間調適。
由於涉及性侵,社工安排進行驗傷,案件也正式進入司法程序。沒想到爸爸一獲知消息,立刻前往中國投靠友人,案件進度則停滯至今。陳湘妤說,她查過法條,知道強制性交罪的追訴期是 30 年,「事件爆發時我是 14 歲,所以到 44 歲前都還有機會。」
「熟人之間的性侵,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難。」雲林地方法院庭長王子榮表示,熟人性侵案中,受害者可能因為情感、經濟或利益關係依賴加害人,他經手的案件中,甚至發生過被害人遭侵犯後,仍可以與加害人如常相處;如果法官除了被害人的證詞外,找不到其他的證據,「這時候我們所受的訓練就是罪疑有利被告,如果沒辦法確定證據,我們可能就是往無罪的光譜過去。」
「所以會不會有些被害人就沒被看見?真的可能會有,那這怎麼辦?這是(司法)不完美的地方。」他坦承。
王子榮的說法直指一個殘酷的事實:部分性犯罪的案件即使進入司法程序,也可能因證據不足,最終加害者不被起訴或無罪。怡玲的經歷就是如此。
怡玲回憶當初之所以提告,是因為和加害者對質的過程中,對方丟出各種理由和藉口,還暗示這並不是第一次,這讓怡玲嚇壞了,她想著其他被害者們的處境,決定訴諸法律處理,「這件事情不可以再發生在別人身上,或許提告可以阻止他。」
雖然律師提醒怡玲接下來可能會有哪些流程,但一切還是讓她覺得很不真實。例如從找律師、報案、看醫生、到做各種鑑定,「有好多陌生的人跟機關進入你的生活。」要跑完這些程序,她得向公司請假,從日常抽離出來,「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個步驟,要去完成,都更證明整個過程的漫長。」

又或者是進到偵訊室時,她形容「那是平常只會在影集裡看到的空間」,當發現自己講的每個字都會被記錄在電腦上時,有種超現實感,完全沒有心理建設會經歷這些事情。
「漫長的過程、加上發生這麼多讓人感到奇妙的事情,都是一種門檻。」怡玲提到,「我當時也沒辦法做決定,是要喊停,還是我要繼續往前,就只能每天過日子,努力往前把這些關卡闖完。才終於理解到為什麼大家會說法律程序就是對受害者很不利。」
案子最終不起訴,怡玲和律師討論後決定不再繼續,「因為我好累了。」而記錄著她試圖證明自身受到侵犯的不起訴書裡,「有很多句子比較不是針對事情,比較是針對我這個人,譬如我的年齡、我的學歷、我的工作經歷、過去的交友經驗,應該要有能力讓事情不會這樣發展。」怡玲無奈地說,「我理智上知道這些東西不是那麼的公正,不要讓這件事影響你自己,但很難。」
證據太少、審理太主觀 性暴力判決常有爭議
檢視近一年的性暴力案件判決書中,不成立案件的法官判決理由,常見「只有告訴人的證詞」、「告訴人證詞前後不一」和「告訴人的反應不像遭到侵害」。王子榮解釋,和大部分有著客觀證據的案件相比,性犯罪案件主要都是由告訴人開口描述被侵犯的過程,才開啟後續的調查,因此必須高規格審視其證詞,並搭配其他的證據,例如告訴人與被告的社群對話記錄、告訴人的精神鑑定結果等,綜合評估後才能做出心證(指法官最後做出的結論)。


如果告訴人的證詞已經非常具體,難道不足以定罪嗎?曾在臺北、彰化地檢署擔任 10 年檢察官的律師陳宗元表示,最高法院過去曾做出一項見解,多數性犯罪只有當事人在場,事後常會各說各話,所以不能只以單方的說法作為唯一起訴的依據。也就是說,如果只有告訴人的證詞,又找不到其他證據,最後多半是以不起訴處分。
王子榮則以貪污案件舉例說明,通常檢察官會提出上百件被告違法的證據,其中包含證人的供詞、書證、匯款證明等資料,;相較之下,性犯罪案的證據平均才 6、7 項,這麼少的證據量要達到足夠定罪的門檻,很不容易,「性侵案還是需要證據,沒有辦法憑著感覺,就算你覺得(被告)很可惡、被害人很可憐,但當被害人開啟了陳述之後,裡面的東西都必須去檢驗。」
陳宗元指出,性犯罪案件對證據的要求,原本就比其他類型案件還寬鬆,「所以臺灣檢察官的平均起訴定罪率大概在 95%,但性犯罪案件定罪率大概只有六、七成」,中間這段差距,就是檢察官在起訴時已經是放寬心證,到法院之後,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或法官不採信,又被認定無罪。
「你會發現為什麼不同案件有著類似的證據,結果卻完全不一樣,其實只是因為審理人員的感受不一樣。」陳宗元認為,這也是判決結果常被詬病的主因,過去在司法官學院受訓時,他們並未受過審理、判斷性犯罪相關案件的訓練,心證的形成都是透過經驗累積,「那個東西別人沒辦法教,只能在不同案件中累積自己的一套標準,說到最後其實就是一種感覺。
READr 也以近一年判決書的七種性暴力關係案件為例,看兩造說法、以及法官以哪些理由駁回告訴人的提告。
「不符典型受害形象」被害人面對二次傷害
現行的司法制度除了無法盡數將性暴力違法者繩之以法,調查、審理的過程還可能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。
July(化名)的案子也以不起訴作結,她相識 10 年的好友、曾經的約會對象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侵犯她,事後 July 質問對方「為什麼我說不要,你還繼續?」他竟付諸一笑「可是妳的身體很想要啊!」直到她反覆強調不要就是不要,對方才在 LINE 的對話中承認犯行、為此道歉。
July 幾乎馬上就決定要提告,當天晚上前去驗傷,走完程序後,等同完成報案流程。她原本決定,如果對方願意接受諮商,並上一定時數的性別課程,雙方可以和解收場;結果他的朋友突然翻供,矢口否認性侵,甚至反指控她只想要錢。
但最讓 July 受傷的,是檢察官訊問的內容。「明明有對方承認犯行的對話記錄,檢察官卻一直問無關的問題:你們是砲友嗎?你那時候有男朋友為什麼要跟他發生關係?被告說你嫉妒他的女朋友,所以才告他,妳有什麼想法?」July 過去上節目談論性玩具的經驗,也被朋友視為證據提交出去,「她(檢察官)就問,性玩具是怎樣?被告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女生,你什麼都很敢說,什麼都很敢做,他被迷得神魂顛倒,才會情不自禁做出這樣的事情,妳有什麼想法?」
「(檢察官這樣問)根本就是加害的代言人,你今天是想要釐清事實,怎麼會是去問這些事情,我覺得超傻眼,妳是對方律師嗎?」July 無奈道,當初選擇走司法程序,就是不想用公審或其他方式懲罰加害人,希望能透過諮商或教育的方式,讓朋友認清犯罪該負的責任;然而走完訴訟的結果,卻是受到司法體制的二度傷害,當初期待矯正或教育的效果全沒發生,「這真是爛透了。」
此外,July 中午遭性侵,當晚先去驗傷,地檢署的不起訴書指出,以其未在當天立即報案,質疑是否有被強迫,她的律師張育瑄提出再議審查,高檢署即回覆「地檢署似有誤會」,但還是主張 July 事發後的態度不似受創,維持不起訴。張育瑄指出,被告藉由提供雙方過去親密的照片、強調 July 性開放的立場,以及兩人事後仍有聯絡等理由,試圖營造 July 並不符合典型被害人的形象,最後檢方也採信了。
為何檢察官和法官如此看重告訴人在案發後的反應?陳宗元解釋,性犯罪案件的證據太少,因此告訴人事發當下的情緒,會被當成關鍵的證據,完美被害人模板於焉出現,「然而,每個人面對恐懼的反應本來就不同,熟人性侵案件中被害人也可能會出現矛盾的舉動,這些都再再證明完美被害人模板是錯誤的想像。」
性別運動蓬勃 改革風氣吹進司法界
近年性別運動蓬勃發展,也對司法從業人員造成影響。律師林家萱就注意到,雖然臺灣 metoo 運動起步較晚,但過去社會爆發的性別案件,或是前幾年在輿論引發熱議的國外知名漫畫「我幫強暴犯做了早餐」等作品,都在司法界掀起一陣討論。她發現愈來愈多法官跟檢察官在訊問時非常小心,盡可能不去觸碰被害人的傷口,或是同理被害人可能會基於自我保護機制,出現違反常態的情緒和思考模式。
張育瑄補充,實務上的確有部分法官在審理性犯罪案件時,並不會將告訴人遭侵犯後的態度變化視為重要的證據,而是比較在乎被告為什麼認為對方同意和他發生性行為,也就是回到性犯罪的核心問題,「是否有違反被害人的意願。」
王子榮表示,過去法官社群存在「裁判書類文化」,意即評價一個法官的好壞,就是看他的判決書內容,「看你寫的文字有沒有很優雅、公正,能不能引述很多實務見解,或是逐一反駁被告的辯詞,寫到他翻不了身。」司法官訓練不會要求學員如何判斷性犯罪案件,只強調要寫得一手漂亮的判決內容,因此至今仍有法官習慣在判決書中一一駁斥告訴人的證詞,「如果告訴人真的曾經受到侵犯,法官的舉動正是直接給予二次傷害。」
近幾年,法官在撰寫案件不成立的判決書寫法出現了一些轉變。王子榮表示,很多法官不再逐項回應告訴人的證詞,而是直接寫出結論,「證據不足以證明到有罪的門檻」。而面對 metoo 運動帶來的效應,王子榮認為,雖不至於會左右判決結果,但有可能會影響刑罰裁量,且審理人員針對這一波 metoo 帶出來的案件,應該會處理得更細膩謹慎。
不過,即使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離訊問,或是在地檢署設置「溫馨室」,讓告訴人能在溫暖的特定環境內接受協助,避免受到二次傷害,但王子榮坦言,司法仍是非常不友善,「告訴人重新陳述自己的遭遇時,就是要接觸自己的創傷;最終走到審理程序時,可能還得面對檢察官和被告律師輪流提問,甚至被揶揄、攻擊,這些事情想到一定會卻步。」
性暴力案件蒐證困難 律師認為司改有極限
此外,司法存在它的極限。陳宗元表示,法律人常說「舉證之所在,敗訴之所在」,意思是當事人想主張對自己有利的事實,就必須負擔找出證據的責任。性犯罪有其證據取得困難的特性,因此被害者事發當下如果能搜集到愈多證據,訴訟就愈有可能勝訴;然而就他任職 10 年檢察官期間的觀察,雖然被害者對於提告愈來愈不感到羞恥,但仍欠缺基本的蒐證能力。
張育瑄則認為,被害人之所以欠缺蒐證意識,一方面是沒有接收過相關資訊,另一方面也是遭侵犯後的自我保護機制,「大家比較會採取一種逃避的心態,因為收集資料的過程,其實就是不斷地自我傷害;或是合理化對方的行為,說服自己其實也沒那麼討厭加害者。」因此,被害人通常對於蒐集證據和參與訴訟,都比較消極。
陳宗元指出,除了司法人員辦案時應展現同理心,不要讓告訴人覺得不舒服之外,司法改革的空間並不多;反而是性平教育的推廣,教育大眾改變觀念,被侵犯不是被害人的錯,再來就是第一時間的蒐證,像是驗傷、錄音錄影、身心科就診紀錄、和被告在事後的對話內容等,都能在訴訟中起到關鍵作用。
林家萱則認為性平教育應更著重在事前預防。她表示,每次受邀去公司企業開課,最常被指定的主題就是職員遭遇性暴力時,該如何蒐集證據;另外她也常在課堂上強調,性犯罪案件不成立,並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,往往只是找不到足夠的證據去支撐證詞,希望社會能以同理心接納被害人,而不是給予批判。
申訴機制昔漏洞多 性騷受害者求助無門
而除了訴諸刑事訴訟,張育瑄表示,如果被害人遭遇的案子是屬於告訴乃論罪,例如性騷擾等,又不想要花那麼多時間、金錢成本去提告,她也會視被害人的身份及受害場域,建議對方進行行政申訴。

例如在職場的話,就找公司申訴;如果是學校,可以向校內的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」申訴,同樣也能達到懲戒加害人、捍衛自身權益的目的。
但縱使有管道可以申訴,過程卻也不見得那麼順利。
徐容萱(化名)4 年前曾遭受職場性騷擾,當時她在一間媒體擔任攝影組實習記者,因為採訪比賽認識了業界資深的攝影記者,「那時候我不會騎車,攝影大哥就問要不要搭他的車去新聞現場,我想說蠻省事的就答應了,結束後也有順利回到宿舍;但之後某一次,他載我回家的途中經過他家,就說他要回家拿東西,叫我跟他一起上去,我很害怕,只好偷偷開手機的定位,並跟朋友報備行蹤。」
「結果一到家,攝影大哥就跑去洗澡,留我在屋子裡乾等半個多小時;最後雖然他洗完澡後有載我回去,但就覺得怪怪的。」壓垮徐容萱的最後一根稻草,是攝影大哥之後載她回學校宿舍,要求其把紮好馬尾的頭髮放下來讓他看看,她覺得極不舒服,並向主管回報,沒想到主管的反應竟是質問:你為什麼要搭他的車?
徐容萱回憶,主管還告訴她,該攝影大哥平常會去嫖妓,應該不至於對小女生做出踰矩的舉動。當時她才就讀大學一年級,看到主管如此反應,便自我反省「都是自己的錯」,所以完全沒有思考後續是否要申訴或提告。
孟萱過去在學校陪伴同學在性平會申訴性暴力案件,對校方的態度也非常失望。她就讀大學時遭教授 PUA 兩年,在教授離校後便陷入長期的憂鬱狀態,甚至無法完成學業,但當時的自己並未意會到教授帶來的傷害;幾年後,該教授再次聯繫她,詢問是否願意替他工作,孟萱決定試試看。
在他們開始共事後的某一天,孟萱不經意看到教授和她的學姊傳送曖昧訊息,「在那個當下,有一種東西竄起來的感覺,我意識到老師原來也會對其他女學生做曾經對我做的事,然後我現在生命裡面的困境可能跟我曾經的經歷有關。我是在那個瞬間突然有種通了的感覺。」
孟萱提及的「老師曾對她做過的事」,是她在大學加入該教授指導的雜誌實作團隊所發生的事。一開始他會在晚上提出喝酒的邀約,兩人聊聊生活、課業和心情;接著,教授會以談工作的名義約她出去,並提供接案機會,兩人在校外的接觸愈來愈頻繁,「漸漸的,他提什麼要求我都不太會去懷疑,有時候會有點過於親密的接觸,比如說摸頭、摸肩膀、摸腿,甚至他會脫光自己的上衣,趴在床上,要我幫忙按摩。」
「我自始至終都說服自己,老師很辛苦,如果我可以多讓他舒服一點,也沒什麼不可以。」孟萱後來才發現,這是一種漸進式的控制過程,教授會在指導的過程中循循善誘,信任一個人應該要做些什麼,如果不從,他就會說「你怎麼那麼不信任我,那你這樣要怎麼當好一個編輯?要怎麼教學弟妹?這樣是沒辦法成為我的夥伴。」她為此常感到焦慮,想方設法符合老師的喜好。
孟萱終於釐清,長達兩年的 PUA 經歷影響極大,而自己竟然是在離校這麼久之後,才意識到這段傷害,她後續透過諮商慢慢走出陰影。
進行諮商一段時間後,有另一個同學跟她聯絡,透露自己剛被教授帶到旅館猥褻,「我跟她說我完全相信妳,我曾經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。」孟萱之後做了決定,無論同學接下來會做出什麼樣的行動,她都會毫不猶豫地予以協助,要出庭作證、曝光都沒問題。
奇怪的是,同學準備提告的消息走漏風聲,被學校知道了。教授跑來找孟萱對質,她被迫再次與加害者同處一室。
「系主任為了保護教授(加害者),還私下說我壞話。」孟萱說:「他說我的婚姻不正當,私生活混亂,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女人。說老師很關心我們,幫助我們得到一份有酬勞的工作,還這樣背叛他。」孟萱不理解,系主任是整個組織結構裡最應該要去接住受害者的人,卻沒有做到。
「我是直到這半年,離開那個地方跟工作後,才發現自己非常的恐懼,那恐懼已經不再是針對老師的事,而是針對共犯結構,讓我非常恐懼職場,讓我意識到沒有人可以接住我們、也沒有人可以保護我們。」孟萱坦言,雖然性平委員很專業、性平會也決議該教授永久不得聘任,且同學提告的案子也確定起訴成功,但她認為校方召開性平會的過程有瑕疵,很有可能導致受害者遭到二次傷害。
性平三法修法 增加受害者申訴選擇
今年 7 月底,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、《性別平等工作法》、《性騷擾防治法》修法陸續三讀通過,重點包括擴大適用範圍、建立外部申訴管道、加重裁罰以及增設被害人申訴與心理支持。徐容萱和孟萱面臨過的困境,未來或許都有解方。
林家萱舉例,《性別平等工作法》在修法後,規定受害人如果不服公司性平會申訴結果、或遭受雇主騷擾,可以直接向勞工局申請調查。她在實務上遇到的職場受騷擾者,多半不信任公司的調查制度,此次修法提供受害者多一個選擇,也增加他們的申訴意願。
至於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,過去已有公權力介入申訴的機制,此次修法只簡化流程,讓被害人不需在漫長救濟過程中反覆遭傷害。但在權勢性關係部分有了明確的規定,禁止未成年師生戀,如果是成年學生,校長或教職員工不得利用不對等權勢關係發展親密關係。
不過,王子榮認為,目前針對性犯罪修法雖有進展,但整體而言仍是過度著重在事後的修補機制,事前的預防才是治本之道,例如推廣性平教育,讓孩子從小就生活在尊重身體自主的環境裡;尤其性犯罪常常存在於具有相互依存的親密關係,不只是司法,而是包含社政、家庭等資源全數到齊,才能有效預防憾事發生。
「大部分的犯罪案件都不會質疑被害者,唯獨性犯罪案件例外。」張育瑄表示自己所經手的大部分案件,只要作為擔任被告的辯護律師,毫無意外都是被外界批評的一方,「大家一定會覺得你今天被告,一定是做錯事才會被告」;然而性犯罪卻剛好相反,反而是被害人被質疑提告動機。
另外像是被害人要求和解金或損害賠償,也會被批評說:「你不是講性自主嗎?不是講貞節嗎?怎麼還談錢呢?這麼俗氣。」張育瑄認為,外界對於性犯罪有著純潔想像,被害人如果和錢扯上關係就不夠完美,這樣的觀念反而會對被害人造成更多的傷害。
Metoo 大浪襲來 接下來呢?
今年 5 月,臺灣爆發 Metoo 運動的浪潮,3 個多月間不少形象良好、位高權重的知名人士哽咽道歉、或是揚言提告、抑或消失在公眾視野。隨著討論熱度逐漸降低,那些勇敢在身上標記 #metoo 標籤的人們,有人選擇自我消化傷痛、有人還在思考下一步,有人在體制內的求助已告一段落。
雖然最終加害者不起訴,但怡玲說,她不後悔提出告訴,畢竟她這麼做不是為了自己,而是為了不讓悲劇發生在別人身上,「我提告的時候就不覺得會贏,結果對我來說也不重要,對方判三年五年、有沒有賠償,都沒有辦法把他對我做的事情取消掉。」
如果有人有類似經歷,正猶豫要不要提告,會給對方什麼建議呢?「我會很坦白地告訴對方我的過程有多難,會有很多不舒服,有多痛苦,它不是一條容易的路。」怡玲說,「但最後要做決定的還是你自己。這件事情的本質是有人侵犯了你,把你的一些能力奪走了,你會覺得一切都失去掌控,但你要慢慢學會做決定,慢慢找回自己的主導權。」
Emma(化名)的案子還在偵查庭,她被才藝課老師的弟弟侵犯,歷時近七年的性侵與騷擾因為事發地點不同,被分往三個不同的法院審理。同樣的事件敘述,她要向三個不同的檢察官說明、接受訊問或質疑,「每次開庭都像是在做同一件事,好像是去面試三個公司,看誰要錄用你、要幫你。」
曾經以為只是去赴朋友的酒局,卻遭加害者壓制性侵,Emma 不敢出聲也不敢動,只能一直掉眼淚;曾經因為朋友明知她遭到加害者侵犯,仍選擇跟其出遊、聚會。看著合照裡沒有自己的身影,Emma 吞了幾十顆藥,只求能失去意識,不再目睹令人傷感的訊息。面對進行中的訴訟,她說,「最不舒服的已經過了,我只是把他講出來而已。」
第一次偵查庭至今快半年,Emma 說,自己是在幾個禮拜前,才確定提告是她希望的結果,「雖然臺灣的法律常被批評很爛,但我覺得還是有部分人是相信法律,會因為法官判他(被告)有罪,所以他有錯;他(被告)被判無罪,所以他是無辜的,有很多人是相信法律判決出來的結果。」
等到有一天判決結果出爐,不管老師的弟弟有沒有被判刑,Emma 說她還是會用自己的方式,讓共同的朋友或認識對方的人知道他曾做過不好的事,希望他不要再去傷害別人,或至少,女生能因此離他遠一點,保護好自己。
「我需要他知道自己犯錯,而且不能再犯。」 Emma 強調,「這種錯不是他說一個對不起,就可以過去、就可以去侵犯下一個人,他必須要覺得這懲罰是痛的。」
引用資料
READr 運用司法院判決書系統 API,搜尋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7 日,曾在法律程序中討論過是否為違反性騷擾防治法、刑法 228 條(權勢性交猥褻罪)的案件,不包括司法院判決書系統判定不公開的資料,共 686 筆。人工標記分析資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