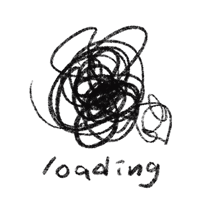李昀的幻聽持續出現在腦海裡,但她試著將這些聲音變成腦海裡的背景音樂,不至於過度干擾她的生活。不過,有些人的幻聽症狀卻讓他們走向另一條路。
「我需要用火燒我自己的身體,治療我內心的創傷。」這是 A 腦海裡的聲音,他從國中開始出現幻聽,就醫多年卻未見好轉。那天聲音再度響起,他打開寺廟裡的點香器點火引燃,火勢竄起,他仍跪在供桌前膜拜。
B 則聽見不同聲音:「快點去搶劫,到監獄住,我就跟你做愛。」即使他持續服藥規律治療,幻聽仍未間斷,最後,他決定聽從腦中的聲音,希望藉由搶劫入住監獄。C 則是長期有失眠、幻聽現象,常聽到有人說他「瘋掉,去死」的聲音,由於長期聽見這些幻聽,害怕到無法睡覺,最後發生縱火事件。
這些別人聽不見的聲音,建構出只有他們才能理解的世界,而成為一個社會眼中的瘋子之前,他們都曾努力「當個負責任的病人」。
每當社會發生重大案件,精神病的污名就會再度被強化,去年底攸關精神病人權益的《精神衛生法》修法通過,就遭到許多批評,像是:「精神病就像未爆彈隨時會發作」、「滿街精神病患者砍人」等,也常質疑他們沒有就醫吃藥,甚至「有病就該送醫關起來」。
為了還原這群人的面貌,我們試著透過司法院判決書裡精神鑑定的內容,找出犯下重大刑案的精神病患者就醫的歷程、家庭關係、經濟的影響。從近千份判決書中可以發現,他們長期困在疾病裡,這之中就醫、住院數次、規律治療、吃藥,甚至高達 15 年以上,卻不像大家以為地可以順利成為「正常人」。

當然也有曾經就醫,最後卻中斷治療的案例,他們常常伴隨家庭支持薄弱、經濟困頓的問題。例如其中一份判決書中提及:甲OO患有思覺失調症長達 9 年,有多次住院紀錄,家境困難,父親長年在外,只能依靠母親跟政府補助過生活,甲OO與家人關係疏離,發病時流浪在外,必須仰賴乞討維生,因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病情而停藥,且不再回診。
當醫療端無法提供有效的幫助,家庭端也無法給予支持,患者便容易孤立無援。更別提有些人的壓力源就來自家庭。
李昀從小跟家人關係就不好,小時候的李昀,甚至會準備逃難包,隨時準備逃家。她回憶,小時候有次坐在家裡走廊中間大哭,家人穿梭而過,彷彿沒看見她,「這麼可疑的行為,大家就真的路過欸,我那時忽然驚覺要自立自強,不能依賴別人,不期待就不會受傷。」
創傷持續累積,卻無法說出口。李昀從 14 歲開始自殘,一直到 20 歲的時候,被學校發現並通報,「隔天我去學校的時候,老師、同學都知道了,我被社會性死亡,每個人都很小心翼翼地跟我說話,有種全世界都背叛我的感覺。」
「我的人生,從發病那一天就結束了。」李昀苦笑地說。

「大部分的暴力,都是以愛之名行之。」在傳統家庭壓迫數 10 年後終於解脫的王修梧,緩緩說出這句話。
他從小就處在混亂的價值觀裡,九〇年代的思想解放,王家衛的《春光乍洩》、李安的《囍宴》,是他最愛的電影,他在那個螢幕裡,看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;但與這些價值觀相左的家庭、教會,讓他產生自我衝突,「我看到這些畫面,就會覺得我眼睛髒了、耳朵髒了,不停地用沐浴乳搓揉,最後耳道都塞住了,我發現我聽不到聲音,我媽帶我去看兒鼻喉科,最後才發現,我應該看的是精神科。」
跟許多傳統家庭一樣,認為同性戀是種錯誤的性傾向,媽媽的關心反而讓他更有壓力,「我媽為了讓我能夠更像男人,她會找她朋友的小孩,那種陽光正向的小男孩,然後帶我一起去打籃球,但我超討厭打籃球的啊!」
用錯方式去愛,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。王修梧的家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,連帶的精神科醫師、心理治療師、牧師都是基督徒,認為同性戀為雞姦者,在長達近 10 年的過程裡,他們相信必須將他「治好」。
王修梧拿起厚厚的病歷記錄資料說,精神科醫師最早的診斷名稱為「潛伏性精神分裂」,診斷內容則是:「性偏差、思想怪異。」
同時,病歷記錄還夾雜媽媽私下寫給精神科醫師的信:「修梧說上帝的寶血已經洗盡他的罪,他已經潔淨了,但魔鬼的心還是一直告訴他,他很髒,修梧每天都很痛苦。」心理諮商師的信則寫著:「自從上次增藥以來,修梧一天比一天更加煩躁焦慮,除了睡覺以外,其他時間都坐立不安,他覺得自己被男性精子污染,雖然他有聖經的話語可以對抗,但還是感到非常痛苦、害怕、焦慮。」
在那段時間裡,王修梧一直被困在自我否定的牢籠,「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骯髒的罪人,這樣的想法也透過精神科醫師、心理治療師、牧師,越來越強化。」
同時他也努力作個好病人。「我其實不太喜歡吃藥,因為會讓你腦袋沒辦法思考,像被灌漿糊,但我媽都會把藥粉磨碎塞進我的餐點裡,所以我透過她的協助,是個良好順從性服藥的病人。」他諷刺地說。
但即使準時吃藥,並沒有緩解他的痛苦,或是就此改變性傾向,「有天我媽幫我拿藥之後,落寞地看著藥,問醫生說:『已經吃了一整年的藥,怎麼還沒好?』醫生只回:『因為他已經變成精神分裂症了。』」
吃藥吃不好,就只能更進一步住院治療,他回想當時住院經歷,整整兩週意識都是朦朧的,因為使用較強的鎮靜藥物,「對於未成年人來說,還真的特別有效果,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出院前一天,照顧我的護理師,看著我哭出來。」
「從他的眼神中,我看到了自己,那時候我才意識到,原來我是一個應該要悲傷的人。」王修梧說。
五月的母親節,在學校學畫康乃馨、折康乃馨,回家送給媽媽,是孩子們常見的課堂活動。但王育慧的經驗則有些離奇:小學二年級的時候,老師要他們折康乃馨,紅色代表媽媽還在世,白色代表媽媽已經往生,她跑去問老師:「有沒有灰色的康乃馨?」因為媽媽看起來像活著又像死了。
從 9 歲開始,王育慧慢慢理解自己的媽媽不太一樣,她生病了,而自己必須從女兒的角色,成為照顧者的身份,一直到現在 40 歲,她成為居家護理師,仍走在照顧思覺失調的媽媽這條路上,看似沒有終點。
社會長期對精神疾病患者有著刻板印象,而身為患者的家屬,身上彷彿有著洗不清的原罪,必須承擔所有照顧責任。READr 從近千份判決書裡,試圖還原精神疾病患者經歷的困境,除了來回醫院跟家之外,家庭支持薄弱是最常看到的困境。作為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,他們經歷了什麼?

「在家庭支持變得薄弱之前,已經有來回好幾次的挫折跟衝突。」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社工督導謝宜恩指出,社會把支持精神病人的責任都放在家庭身上,一旦家庭支持變得薄弱,生活就會垮掉,「可是一個理想的社會,應該是就算家庭支持薄弱,社會支持系統應該強到足夠維持他的生活。」
她舉例,自己曾經遇過的個案家屬,「他過去一直非常努力的想要理解生病的哥哥,但被攻擊之後,家人們就決定從此跟哥哥斷絕聯絡。」社會只看到最後斷絕聯絡的結果,「但前面很多的衝突,都只有家庭在磨,沒有人介入,出事就是自己想辦法,送醫後再從醫院回家,兩個人在生活裡面面相覷。」
謝宜恩分析,當家庭支持足夠,精神病患者其他生活面向也會隨著改變,所以以家庭為中心提供服務非常重要,而家庭最常遇見的困難就是「求助困難」,包括:不敢求助、不會求助跟求助無門。
她舉例,常常碰到不敢求助的個案,擔心從此被貼上標籤,「有時候甚至家人都拿刀出來了,還不敢報警,擔心鄰居會怎麼想。」再者,其實從小到大都沒人教過,家人生病該怎麼處理,「像是生病的家人覺得自己被下毒,你要怎麼跟他對話?就沒有毒啊!你只會覺得他瘋了。」社會缺乏精神健康教育,當事者無法覺察自己的困難,就連家人也無處施力。
謝宜恩直指,社會缺乏支持系統,雙北相對其他縣市資源比較多卻仍不足,「今天我接到南部的求助電話,我就會想:天啊!我完全沒有資源可以介紹給你欸!」不管是醫療或是社區復健中心,資源都非常少、多樣性也少,「很多時候你想求助,但你接觸不到資源。」

「從小我們家就有很多很吵的聲音,例如我媽晚上不睡覺,就把電視開很大聲、對著電視機不停講話,或是用力甩門、洗碗洗很大聲。」因為「黑毛仔」不斷對著王育慧的媽媽叫囂、攻擊,她必須用更大的噪音蓋住這些腦海中的聲音。
王育慧 9 歲的時候,爸爸告訴她,媽媽生病了,「我當時似懂非懂,我只知道媽媽去住院的時候,我就會鬆一口氣,可是我又對於我鬆口氣的感受,心裡感到很抱歉。我覺得她在的世界,我碰不到。」
還沒好好長大,就被迫成為大人。媽媽是思覺失調患者,病情反覆,王育慧的生活裡,媽媽的角色始終缺席,「我第一件內衣是我好友的媽媽買給我的,我妹妹的內衣,則是我代母職,陪她去買的,甚至小時候的家庭聯絡簿,都是我自己蓋章。」
不僅如此,她還必須負擔照顧媽媽的責任。在王育慧國三的時候,媽媽離家出走,失蹤 18 天才一臉憔悴地回家,「那幾天我跟妹妹一下課,爸爸就牽著我們的手,到處找媽媽,從三峽、鶯歌、土城、板橋,到處敲門問有沒有看到我媽,還有人說:『你怎麼沒有管好她?』或是一有人打電話說:『好像有看到一個女人,在路邊吃 phun(臺語:餿水) 。』我們就會馬上衝過去看是不是媽媽,我爸他每天回家都在哭。」
「我當時其實不知道我希不希望找到她。」王育慧坦言,整個童年都不快樂,甚至國中的時候變得很憤怒,「我媽瘋起來的時候,就會用力敲門,我還要叫我妹從陽台逃出去、把菜刀藏起來;我爸上夜班的時候,我們必須把房間門反鎖,很怕晚上被媽媽殺掉。」
在那樣漫長的折磨裡,她形容自己就像處在孤島裡,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。「當吃藥都吃不好,就會感到很絕望。」
從她小時候,爸爸必須同時照顧生病的媽媽、年幼的小孩,到王育慧必須姊代母職,甚至分擔照顧媽媽的責任,「不管出什麼事情,我們家都是靠自己,我覺得沒有什麼(政府)資源可以進來。」不論是康復之家、社區復健中心,那些政府提供的資源都離他們太遙遠,「我媽媽住康復之家的第二天就失蹤,那天還是母親節,我們在山區找了她整整 6 小時。」
「很多資源看起來都很棒、很進步,但大家都忘了,這些病人要不要去、怎麼去、誰陪他們去?」王育慧說,不論是自己的媽媽,或是之後身為居家護理師接觸的個案,「他們的起點就在家、在那張床上,他們根本不願意走出家門。」在缺乏社區支持的資源下,即便媽媽定期吃藥、回診,「但她沒有好起來,活得不像一個人,只是在呼吸而已。」
在晦暗無光的日子裡,爸爸卻持續點燃希望。「我爸的包容度很大很大,幾乎逼不得已,不會讓我媽住院,他做很多的變化,讓這個家變得彩色,也給我們很多快樂跟堅強。」
王育慧分享,媽媽以前很常半夜離家出走,「但我跟爸爸是開著車默默跟在媽媽後頭,觀察她會不會過馬路,有沒有狀況,等到兩三個小時過去,差不多該帶她回家休息,我們就會弄個不期而遇,開車經過跟我媽說:『欸你很面熟喔!你怎麼在這裡?』用這樣溫和的方式把我媽帶回來。」
在這個過程裡,他們試圖去理解媽媽的世界。有次媽媽在外面滿頭大汗卻不停地掃落葉,「我問她:『為什麼一直掃,你不累嗎?』她回我:『因為掃地可以讓我腦袋清醒。』那一瞬間我很羞愧,我覺得我都做錯了,只有給藥而已,但我媽在用自己的方式,救她自己。過去我們靠近不了,就離她遠遠的,我們很孤單,作為子女的愛跟補償都沒有,但我媽其實也很孤單。」
王育慧一家人發展出自己的照顧系統,除了監視器 24 小時運作,他們三人每天輪流值班照顧媽媽,甚至並不只把她當作病人而已,更是維護媽媽的「自由意志」。
7 年前,王育慧決定要去花蓮工作,但媽媽狀況卻非常糟,一旦她離家,沒有人可以分擔照顧責任,媽媽就必須住院,她回憶起那天爸爸跟媽媽的對話:
爸爸:「你不住院嗎?你又不能為自己做決定。」
媽媽:「我為什麼不能為我自己做決定?我真的不會再亂跑出去。」
一陣沈默。
爸爸:「那你要永遠記得這天,這一天都是你的自由意志決定的。」
再度沈默。
爸爸:「不然我去自殺好不好?」
媽媽低聲說:「不要自殺,要去(自殺)我去就好了。」
那一天,王育慧選擇繼續留在家,照顧自己的媽媽。「我很想要走自己的路,可是我真的沒辦法離開,為了支撐她的自由意志,我們付出很大、很大的代價。」
從原本的逃避,到把媽媽視為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」,王育慧經歷漫長的追尋,把媽媽的原本的樣子找回來。她找了媽媽年輕時的好友、超過 30 年的病歷資料,「眼前這個媽媽,你很難去愛她,因為她太怪異了,可是我透過別人的口中、年輕時期的照片,看見她生病前的樣子,她其實也曾經是個很漂亮的青春少女。」

去年底攸關精神障礙者權益的《精神衛生法》修法通過,將在 2 年後正式上路,此次修法著重改變過往「治安管理」的思維,不把資源全放在醫療端上,而是明確定義「社區支持」內容,並建置相關資源:運用社區資源,提供病人於社區生活中所需之居住、安置、就學、就業、就養、就醫、社會參與、自立生活及其他支持措施與協助。透過社區支持讓精神障礙者重建自己的生活,而不是僅在醫院跟家之間徘徊。
不過社區支持具體而言是什麼?「大家對於一個生病的人,無法想像他需要什麼生活,但其實社區支持就是怎麼在社會上生活而已。」臺灣精神健康改革聯盟召集人廖福源指出,「我們要先知道他被摧毀跟剝奪什麼,在支持他的歷程裡,把這些東西找回來。」
廖福源無奈地說,現在社會只考慮到醫療,卻不考慮到一個人出院之後的生活,「疾病只是後來的結果,他可能經歷各種生活的失落,衍生長大後無法自立,我們怎麼協助他的失落跟自立,這是我認為這次修法要做到的,而不再是治安管理的思維。」
《精神衛生法》修法僅是第一步,要改善過往過度重視醫療,卻乏社區資源的現象,除了母法明確定義社區支持,後續如何落實,仍有賴這期間各部會儘速完成相關子法修訂與各項配套措施。READr 遍訪學者、民間團體、立委、當事者,統整出精神障礙者面臨的數個困境,以及未來法案正式上路後,可能帶來的改變。
首先,過去政府重視醫療資源,卻忽略建置社區支持資源。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社工專員李麗芬就指出,目前社區並沒有完整的支持服務,這些個案出院後沒地方去,就只能回家,再加上吃藥的副作用,導致他們無法有穩定的工作,甚至有些年輕時期就發病的個案,「在來回醫院的過程裡,無法去上學,他們的成長過程一片空白,如果社區又無法承接,他就會變得很孤單,家人也無法彌補一個人在社會應該經歷的過程。」
「如果他在醫院裡沒有症狀,好像就等於他沒事了,但現實並不是這樣。」在她過去服務的經驗裡,她認為,更需要從這些個案的邏輯去思考,理解並協助梳理這些思緒,「如果沒有這種支持的話,他們出去面臨很多困難,一旦這些挫折的累積,就更容易引發他的症狀。」
被診斷為躁鬱症的李昀回想吃藥的第一天,整個人變得遲緩,感官跟思考速度都下降,甚至藥物的副作用讓身體逐漸出現問題,「每天 23 顆藥,一把一把含著淚吞,每天低燒、頭痛、全身顫抖、每小時烙賽,我出門一定要坐 Uber,不然就會烙在路上,失能到不行,整個人吃藥吃到像神經病。」
「這都不可怕,更可怕的是沒有好啊!我還是想自殺、我還是聽到怪聲音,但我不疑有他,因為我以為已經無路可退,不吃藥只會更慘。」
「成為一個病人是全全面面的,你不會只吃那顆藥而已,你的痛苦很全面。」藥物除了副作用,生活模式也跟著受限,不能喝酒、要早睡早起、沒有夜生活、不能聽奇怪的音樂、看奇怪的劇,「因為你沒力氣看,你也看不懂,再來會影響心情,不要做任何挑戰,很多事情都被剝奪。」
吃藥好不起來,下一階段就是住院治療。住院的日子裡,失去時間感,重複一樣的生活作息,起床、吃飯、吃藥、放風、折紙蓮花、吃飯、吃藥,「你感覺只是被關在裡面,只記得自己很爛,醫院更強化你是個病人的想法,你出去只會再進來。」
李昀回想,每次出院後,都得重新適應一次社會,連公車都不會搭,對外面的節奏感很陌生,「你最後反而擔心的是沒有醫院收你。」而讓她印象深刻的是,某此住院期間碰到過年,她請假 4 小時回家圍爐,「大家看我的表情都很曖昧,我覺得我讓家人失望,但我很努力了啊!大家對你不期不待,只希望你活著,但你根本不知道活著要幹嘛,這是最痛苦的。」
「大家不相信體制不是沒有理由,就是沒有效!」李昀強調,醫療治標不治本,「沒有路可以選的時候才會選醫療,但把你綁起來到底會治好什麼?把你打昏,每個人都不會犯罪啊。」有些人是不得不住院,「因為社區很爛,爛到你沒辦法活,寧願去住院,這真的很悲慘。」
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秘書長張朝翔指出,臺灣精神病患者平均住院天數是 283 天,每天生活就是排隊吃藥,基本上沒有休閒娛樂,出入醫院都需要申請、家屬陪同,「這等於是社會隔離,等到出院後,他已經失去很多能夠支持他的網絡,他能不能融入原本的生活都是個挑戰。」
國外早期研究就指出這種出院後又再入院的「旋轉門效應」,張朝翔解釋,「出院等於預告他下次一定會再入院,因為住越久,越難適應社區生活。」而國外實證的社區支持系統則提到,要改善這樣的困境,首先要縮短住院時間,第二則是要盡量在真實的社會環境做生活訓練。
張朝翔曾經是醫院職能治療師,最後卻組了一支由精神疾病患者的足球隊,投入社區支持的工作。「我早期在醫院的時候,發現有些個案住了好多年終於出院了,但沒隔多久又再回來,我當時就想知道社區發生什麼問題?」帶著這樣的疑問,他看見社區資源不足、支持模式有問題,「社會常常把他們視為病人,所以我才希望透過 NGO 組織,透過不同的服務,長期陪伴他們。」
重鬱症患者郝天行表示,「我們在檢視精神醫療問題的時候,很常被誤會是反藥物、反精神醫療立場,但醫療確實是一種資源,只是要討論該如何運作。」
郝天行強調,精神醫療有它的存在意義,自己後續就醫過程裡,也有遇過好醫師,透過藥物讓她病情穩定,「應該要討論的是,目前機構化而照護標準化、僵化,甚至住院時濫用束縛等強制處遇的醫療行為,要怎麼改革,就像我的住院經驗,其實是二次創傷。」
郝天行從小就比其他女生來得高大、圓潤,「我常被嘲笑身材、沒有女性氣質,我好像當不成一個女性,我非常努力追求社會對於正常的想像。」除了容貌焦慮,小時候的家庭經驗也造就她的心理創傷。
郝天行由奶奶一手帶大,父親跟母親很少出現,她最記得的印象是:「在我 4、5 歲的時候,我生母會把我關起來,一直跟我訴苦,還會問我:『你覺得委屈嗎?』我被鎖在房間出不去,只能一直看著她。」「生父也很少出現,小時候有段時間常接觸,但我每次跟他見面,都會被打,我姑姑有次親眼看見他一巴掌把我打飛。」
那時候年紀太小,記憶都是歪斜的,她卻清楚記得,被關在房間裡的恐懼,以及從那時候開始的強迫行為,「我從生母的房間走出來之後,都會經過浴室前的地墊,我總覺得它是歪的,一直踢它、調整它,想把它擺正,但不管怎麼調都是歪的,想要離開卻走不開,我很痛苦。」
郝天行曾經三度住院治療,而每次的住院經驗,都讓她受到二次創傷。她回憶自己第一次住院的經過,當時處在恐懼焦慮的狀態,突然覺得很多聲音,於是拿刀往手割下去,被朋友緊急送醫,「我一方面心想我就是瘋子,但又有那麼一點點期待,也許在醫院會有人來安慰我。」
那天晚上,她睡不著,走到醫院大廳,拿著筆往自己手上戳,「我想要讓他們知道我不太好,但我講不出來。」痛苦無法言說,只能透過自我傷害,釋出求救訊號。
護理師看見後大聲喝斥她,並且將其帶進保護室裡,「他們把我綁起來,那時候的感覺,就像是小時候看到我爸,我真的希望這次能做對、能夠被鼓勵,但結果還是被打飛。住院的那一晚,我想要求助,但最後就像是被一巴掌打飛出去,讓我感覺自己很渺小。」
精神醫療有許多問題待處理,而從醫院回歸社區,也往往資源斷裂。長期推動修法、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指出,過去實務上,醫院跟社區無法連結,「醫院往往只有就如何服藥討論,而社區心衛中心可能也不知道負責的區域有誰出院,除非家人知道怎麼尋求資源,不然病人可能就是回到家中慢慢惡化,再次回到醫院。」因此,此次修法重點之一是要協助精神障礙者在出院前擬定準備計畫。
修法後的《精神衛生法》第 33 條就表明: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,應協助病人共同擬訂出院準備計畫及提供相關協助;屬嚴重病人者,應通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派員參與,並應徵詢保護人意見。精神醫療機構也應該將計畫內容通知地方主管機關,以提供社區治療、社區支持及轉介或轉銜各項服務。
從我們收集的近千份判決書中可看到,精神障礙者面臨各種困境,在疾病之外,更常看見家庭支持薄弱、人際疏離、長期受家庭暴力,以及經濟困境,包括低收入戶、長期失業等,這些並非是單一醫療資源可以解決的議題,如何修正社會體制才能接住這些人更該被討論。
「我們最常遇到的是被制度霸凌、制度不給協助。」李昀指出,社會先把窮人變病人,最後再讓病人機構化,「這悲劇是社會造成的,你說社區支持要做多少服務,其實預防更重要。」
她強調,精神障礙者的需求跟一般人一樣,「我們其實沒有差很多,這些『特別』都是被創造出來的。」社區支持不該是獨立排除的設施機構,而應該讓障礙者可以回歸自己的生活,讓他的支持網絡更堅實,「但現在是給他個地方去,把他關起來,用機構化、醫療化控制人,臺灣本末倒置。」
她表示,社區支持是品質的問題,而不是形式的問題,重點應該是讓障礙者有權利為自己做選擇,而且有後援,「你不可能用打斷他的腿來當作保護他,我要的社區支持就是這樣,一來你可以選擇你要活的方式,第二你做錯選擇你可以回頭。」例如臺北市的向陽會所,就讓精神障礙者全員決定會所的大小事,要不要工作、分組討論議題,透過對話促進彼此的可能性。
「不管是日間型還是住宿型資源,都是看得到、用不到。」張朝翔則觀察,政府過去建立這些資源時,沒有考量各個障別的差異性,「精神障礙者使用率佔不到 10%,可是他們佔身心障礙者人數比例是高的,他們卻用不到這些資源。」即便這些機構都稱為身心障礙者服務,但是有些單位並不收精神障礙者,甚至這些人也跟機構提供的服務不相容。
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社工督導謝宜恩舉例,它的設計本位比較屬於肢體障礙者,而不是精神障礙者,為了每個人都能參與而規劃的復健活動,包含摺紙、烘焙,「對有些人來說非常需要,但也有人反映,那太簡單,我去了超無聊。」
「現在不能說完全沒有資源,政府一直在佈建,但我覺得還不夠多元、人力不足。」謝宜恩指出,不管是復健中心、康復之家,都是以復健心態進行回歸社會的活動,但對於出門就會害怕的人,或是根本不願意說話的人,這些不同需求沒有辦法得到適當服務,「會在醫院跟家之間來來回回,是因為社區的網絡佈建地不夠密,多元性不夠高,大部分人的需求沒有被現在的社區資源回應。」
「現在是以一個控制風險的方式在管理。」謝宜恩表示,自己長期負責照顧者專線,很常接到家屬來電說自己家人沒有住院過,但狀況不好,真的需要有人來家裡談一談。但現在的個案管理方式,都是由衛生所列管,再派案給入家服務者,這些看似沒有危急需求但又有困難的家庭,就很難被納入現在的服務體系,「(社區資源)就是固定的框框,你要把不同的人塞進去,而塞不進去的人,就一直在系統外面。」
此外,過去限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才能使用相關服務。廖福源解釋,截至 2019 年 9 月底,全臺約有 20 萬人因精神疾病而領有重大傷病卡,卻不一定能領取身心障礙證明,但許多服務例如社區居住、自立生活支持等,卻僅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才能申請。他強調,光是精神科看診累積人數就 200 多萬人,許多人根本進不到政府資源的系統裡,這次修法也希望讓不敢拿、不想拿手冊的人,也能得到更多社區支持的服務。
而根據修法後的第 23 條也明定,社區支持服務應依「多元連續」服務原則辦理;地方主管機關也應自行、委託、補助或獎勵機構、法人或團體提供全日型、日間型、居家型、社區型或其他社區支持服務,以建構妥善之社區支持機制。另外,也應提供病人家屬心理衛生教育、情緒支持、喘息服務、專線服務及其他支持性服務。
另外,目前精神疾病相關預算不僅少,又高度集中在醫療端。王婉諭就曾整理,以衛福部心口司(現為心理健康司)整體預算來看,2018 到 2020 年扣除口腔衛生、成癮戒治、家庭暴力等預算後,精神疾病防治經費約 2.3 億,僅佔衛福部總預算的「千分之一」。
更重要的是,精神照護系統登入的精神疾病患者約有 13.9 萬人,其中醫院、精神護理之家收治約 2.6 萬人,剩餘的 11.3 萬的精神病人皆生活在社區中,但從 2020 年預算來看,社區端預算僅 13 億,是醫療端的 1/10。
許多社區支持其實都是由民間自主闖出來,包括會所、社區家園、照顧者專線等等,王婉諭直指,政府過去態度比較像沒辦法做、不願意做,於是用委託補助方式鼓勵民間做,「但成立一間會所,補助可能只有 10%,剩下 90% 都要自籌,其實很難有量能再去籌措第二間,所以各地社區支持量能其實非常非常少。」她強調,這次修法要求重視社區支持的服務內容,並且相關資源、預算編列都要到位。
不僅預算不足,連人力也吃緊。王婉諭也指出,衛福部最主要的精神社區服務為「社區關懷訪視計畫」,透過社區關懷訪視員訪家協助精神疾病患者,但每人負擔案量過多,已經是長久問題。
在修法通過後,衛福部心理健康司前司長諶立中曾公開表示,預計 2025 年,在全臺設置 71 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(簡稱:心衛中心),並將聘用 1000 名社區關懷訪視員,人數較從前增加 10 倍。
此次修法也要求各地方政府的社區心衛中心負責個案管理、心理衛生促進、教育訓練、諮詢、網絡聯結等,協助患者能順利與社區支持資源連接。各地方政府也應結合衛生、社政、民政、教育或勞動機關,建立社區支持體系。
「現行的心衛中心有這麼多問題,就是他們就太注重 KPI 了!」身為居家護理師及精障者家屬的王育慧指出,國內整體訪視制度失靈,公衛一個人照顧上百案,被賦予的任務就是醫療,只要有醫療就好;而在健保制度下的居家治療,醫院為了成本考量,居家護理師一天要訪 5 個個案以上,「訪視哪有什麼困難?有活著、有在吃藥就好,但如果你要連結外部資源,像是就業、生活自立等,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時間,生命的改變才是最困難的。」
她接著指出,受限於訪視精神病人的健保給付很少,不足以支撐精神居家護理師獨立開業,目前社區缺乏專責精神照護的精神居家護理所,那心衛中心就應該負擔起這個功能,但目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。心衛中心是政府社區訪視政策的一環,這個起點非常重要,但她強調,不應該過於注重績效、限定人數,未來調整應該保有彈性,除了增加人力,也要改變觀點,「由於障礙者面臨不同困境,制度應該要允許各種奇怪的工作方法可以發生,鼓勵工作者發展多元的支持模式。」
此外,民間團體不斷呼籲,應該拉高心衛中心層級,廖福源解釋,心衛中心就是大的個案管理師,像是仲介,將社區的資源介接給個案,他應該要能整合警政、消防、社政、教育、勞動等各單位的支持服務,才能避免各單位、各服務之間各管各的。
臺灣許多康復之家或社區中心都是私人機構,有自己的評估系統,個案常會遇到被拒收的問題,張朝翔認為,「心衛中心應該要有最高的權限去橫向連結、調動資源。」下一步心衛中心的挑戰,應該是像香港一樣,直接由心衛中心做資源的分配跟管理,統整區域的資源,並且評估個案需求,當真的有需求時,就應該協助進到機構裡,讓資源網絡動起來。
即便修法通過,後續是否真的能落實也有待觀察,廖福源就表示,「沒有預算、沒有計畫都很難做,現在都是先喊出來,政府到底有沒有預算跟人力去撐出修法之後新增的資源,還不知道。」
此次修法仍有些遺憾,例如精神障礙者不斷倡議的「同儕支持」未能入法。同儕支持意味著由病情穩定且受過訓練的精神疾病患者,來幫助其他患者,由於擁有相同的經驗,也更能感同身受,幫助彼此,目前英國、美國、澳洲等都已經實際操作。
「同儕概念不是我們需要被治好,而是我們的人際被剝奪,這其實是個返還的概念,我們盡可能創造支持網絡。」李昀表示,自己的租屋處就常成為身邊病友無處可去的避難所,「你今天想自殺就來我家住,不用只能被迫去醫院,你今天沒飯吃,我就送飯到你家,這都是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支持方式。」透過這樣聚在一起的互動方式,即使不特別做什麼,「他們就會覺得很安心。」
王修梧、郝天行等人則成立臺灣失序聯盟,期望透過過去彼此支持的經驗,成立更有效的同儕支持系統。「我們一直主張把同儕支持入法,但最後就是沒有入法。」王修梧無奈表示,「之前會議上,衛福部回應:『同儕支持當然很好,但因為在有限的資源下,應該把專業的都先佈建起來,再去做其他的。』」
他強調,同儕支持入法才會有資源,讓這些失序者可以使用分配,建立支持系統,但精神障礙者的經驗不被重視,「現在的修法方向,就是讓社工主導,沒有我們的參與,又要幫我們做決定。」
除了這些困境,精神障礙者有更現實的問題要面對。李昀就指出,自己身為倡議者,很容易就被貼上標籤,「出來(為障礙者)發聲,因此找工作有困難。」社會對精神病人的污名,會直接反映在公司錄不錄取、房東願不願意租房的現實問題,「甚至是你狀況不好被迫住院,你的工作就很難持續,你也很難解釋你為什麼消失一個月。」
修法後的精神衛生法正嘗試補破網,但早在修法之前,其實民間團體就自己闖出多元的支持模式,例如伊甸活泉之家的敲敲話入家團隊,當因為精神狀態而出現家庭危機時,透過團隊實際進入家中,陪伴障礙者及家屬度過危機。
對郝天行來說,這(敲敲話入家團隊)是真正讓她感到有幫助的做法,「像是我以前一回家就會進房間,避開跟我姑姑見面,不想讓她看到我不好的狀態,但入家的時候,我可以聽到她的想法,她其實很愛我,不想要我假裝快樂。」
「入家服務不是聚焦在一個人身上的病理問題,而是在聚焦一個團體內部發生了什麼事,生活過得怎麼樣。」郝天行分享自己卡住的生活困境,她的姑姑則分享不知道該如何幫助的焦慮,透過對話理解,「他們不是用病理化看待你的行為,但許多政府機構,其實比較是評估你帶來的治安風險。」
王修梧也是郝天行入家服務的一環,互為彼此的精神支持。
他們在大學時候認識,當時的王修梧離家南下求學,他在大學受到更多思想啟蒙,像是何春蕤的《豪爽女人:女性主義與性解放》,「我開始發現,其實除了同性戀之外,還有更多骯髒的性呢!我也是骯髒的一員,那我們好像也不是什麼少數耶!」因此到大二之後,他便不再有強迫行為。
他跟郝天行也加入性別團體、高雄同志遊行,「接觸這些性別活動之後,我的強迫意念,因為感覺也沒什麼好強迫的,就是化解開來了。」
另外還有伊甸的精神障礙者會所(真福之家),提供日間服務,透過日常團體生活建立關係,並且發展精神障礙者培力計畫、發展同儕工作者,讓精障者用自己的經驗彼此支持;而同時身為精障者家屬及居家護理師的王育慧,則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小鎮社區支持系統。
居家護理師的任務其實只是到家提供醫療協助,但王育慧堅持多做一點。王育慧從過去一對一的「居家治療」模式限制, 逐步發展出「社區」式的精神照護。不只重視個案的疾病症狀,更逐步協助他們回歸社區,包括建立在地社群支持讓彼此分享疾病經驗,甚至連同其他社區入家工作者合作小旅行,讓不易出門的個案及家屬跨出家門;找到友善僱主建立障礙者工作成就感,逐步回歸職場等。
他們團隊成員總共 6 名,負責 360 名個案,橫跨半個新北市。她舉例,她服務的其中一名個案住在泰山,「精神障礙者活動範圍不會離開這區,我就會運用這小鎮的所有資源,整個泰山都是我辦公室,像是麵攤、超商、市場、圖書館、寺廟、教會,它就是沒有圍牆的社區支持。」
她進一步解釋,每到一個小鎮她就會先去拜訪這些「眼線們」,像是巷口的魯肉飯店家會跟她報備說,「今天誰誰誰來吃飯,吃得太油了,我還幫他多加點青菜。」王育慧說,透過這樣的方式,讓這些個案可以去好好工作、好好吃飯,重建自己的生活,「我們這群工作者就是個案的 WIFI,去連結外界的資源、社會安全網,發展出多元的支持。」
「靠小鎮的力量,建立人際關係網絡,也許我媽媽以後就不會走失,一走失所有人都會幫我找回來。」對王育慧來說,肢體障礙者的輔具是輪椅、電動床,對沒有傷口的心理障礙者,輔具則是一段關係裡的信任感、安全感,「這種看不到卻很基礎的東西,才能幫助他們從斷裂的世界,一步步走出去。」
除了日常生活的支持網絡,悅萃坊劇團下的奇異果劇團,則透過「一人一故事」戲劇表演的方式,讓障礙者願意分享自己、聆聽他人的困境,並透過身體演繹出來。
奇異果劇團成員大約 10 位,每位皆是精神障礙者,每週練團時,他們會先分享自己生活的小事、暖身遊戲,最後則是分兩組,一組人說出自己心裡最近的困境,而另一組人則試著將這些故事即興演出來,包括找不到工作的焦慮、夾在老師跟媽媽之間的學業抉擇困難等,透過說出來,讓這些痛苦有機會被釋放。
「戲劇就是呈現一個人的生活,吃飯、聊天、讀書,透過邊講邊聽,你會反思到一些新的意義。」奇異果劇團帶領人的劉怡妏表示,在華人壓抑的社會氛圍裡,痛苦很難被說出來,甚至會被認為是想太多,「這其實是雙重壓迫,疾病讓我們很壓抑,而社會文化又再加深我們的壓力,但透過戲劇形式可能可以學著去釋放。」
「他們有話想說但說不出來,或是很多的感受,不知道怎麼命名。」劉怡妏解釋,因此在說故事的當下,會有主持人去帶領他釐清自己的感受,再加上說故事之前的暖身遊戲,他們知道可以信任對方,犯錯了也沒關係,因此會更願意說出自己的感受;而負責表演的人,除了學會理解他人的痛苦,也在肢體表演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經驗。
她接著說,劇團也會設計很多遊戲,比如「大便遊戲」,讓其中一個人當鬼,他要去把大便抹在別人身上,被碰到的人,要重新整理再去抹別人,大家玩到邊跑邊叫,「它其實有些隱喻,象徵著你不想要、很想躲避的標籤,可是我重新整理後變出新的東西,像是有人就變成水晶球,變成愛送給對方,那都是內在很自然的轉化,你可以從這過程裡,看到他們其實內心有好的盼望,有柔軟的一面願意去給予。」
「很多夥伴玩完這個遊戲後就會說:『我們玩得像瘋子。』」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監事、奇異果劇團帶領人之一的繆珮清笑說,「瘋子」其實是一個好玩、自由的詞,它並沒有真的那麼負面,像這樣的遊戲裡,他們可以很自在,不用去想到社會框架,可以很放心地去嘗試。
繆珮清表示,自己以前也會無意識地用疾病去看待每個人,但久了之後,反而很自然地去看到每個人個性的差異,而不是把所有原因歸咎在症狀上面,劇團 10 個成員就有 10 個樣子。
她也提到,劇團成立 4 年,有些夥伴成長許多,除了穩定工作,甚至有醫生跟夥伴說,要繼續去劇團,因為讓病情穩定許多;另外一個夥伴則是從不太說話,到後來已經可以跟大家自然地互動,「甚至有天還突然打我屁股,我從來沒有被打屁股打到那麽開心過,他已經可以把自己放出來了。」
臺灣家連家創會理事長、奇異果劇團成員之一,同時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吳金蓮,也曾在這樣表演的過程裡療癒自己,她回憶自己接觸戲劇表演的第一天,「因為我一直都是非常嚴肅地過日子,那天老師放音樂,要大家閉眼睛自由走動,一輪過去睜開眼睛,只有我站在原地不動。」
直到老師牽著她慢慢地帶她舞動,她才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很自然地擺動自己的身體,不被限制。這樣的學習經驗其實很漫長,在過程裡去找到沒有框架的對待,並且回頭幫助自己生病的家人,「我就是不斷地學習,想要找出一個 key,可以幫助我哥哥。」
吳金蓮的二哥罹患躁鬱症、思覺失調症 47 年,她回想起,跟哥哥的互動,過去一直希望把他醫好,恢復成家族裡期待的樣子,「我們長達 5、6 年的時間,都在往這個方向努力,運用所有資源跟人脈,就是要把他治好。」
那天她接到通知,哥哥又發作了,她趕忙去到哥哥家裡,「我進到客廳,突然電話鈴響了,我二哥就非常生氣,因為他不想跟任何人接觸,而把電話線剪掉。」
哥哥拿著剪刀,生氣地大吼:「到底是誰做的(把電話線接回來)?」
我:「是我做的,我只是平常想要關心你。你這樣我會害怕。」
哥哥生氣顫抖地像是隨時要翻桌。
哥哥: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多痛苦?」
我哭著說:「我不知道,我真的不知道……」
那一瞬間,長久僵化的關係突然有了改變,吳金蓮的哥哥慢慢放下剪刀,「從那時候我們關係慢慢有改善。」不論是在劇團的經驗,或是長久以來身為照顧者的心得,「在他不斷失敗之後,我們不再逼著他,而是整個家族的人試著去調整心態。」讓他從做家事開始慢慢學起。
拿下「病人」的標籤後,哥哥的狀態反而好起來,吳金蓮的哥哥開始會跟她開玩笑,笑她說「從小就沒膽。」甚至後來哥哥穩定到可以自己重新裝潢家裡,「沒有人相信他可以做到,但他做到了,還自己去挑油漆、議價、談分期付款,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靠近。」
在哥哥死後,她常常會想到她跟哥哥的對話,「我哥跟我說:『如果有空就要常回來,這裡永遠是你的後頭厝。』到最後,我不再是一個常常管他、評斷他好不好的人,我終於找到從照顧者變回他妹妹的途徑,在我哥哥眼裡,我永遠是他親愛的蓮妹。」
社區支持有各種樣態,對於到底實際社區支持如何執行,或是規範內容要到多具體、細節,王婉諭則認為,「並不需要特別規定做什麼,應該是政府負責投入預算、人力,讓這些民間團體的量能可以多元地長出來。」
她強調,各個民間團體提供多元性的服務,讓精神障礙者可以隨著自己的能力、喜好,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,甚至是國外已經開始做的同儕支持服務模式,不只是以專業人士的身份,更讓這些病友先到醫院端,協助他未來出院,這些未來都可以發展,「不去特別規定做什麼,這很重要。」
「精神病人不是永遠都這麼危險、有攻擊性,這必須持續倡議跟和解,當然這過程不容易,包括我自己也不容易。」王婉諭坦言,這麼堅持推動修法,「主要還是因為我們自己的事情,讓我覺得,如果他在一步一步墜落的過程中,假如得到比較有系統的協助,會不會其實能避免這個悲劇。當然有一部分還是希望能夠找到自我安慰,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別人身上。」
「但我也沒有天真到覺得一定可以完全沒有(發生悲劇)。」王婉諭說,修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,後續政府如何落實需要持續監督,「我覺得沒辦法這麼快,可能兩、三年後有機會看到有些不同,但不太能完全落實。」
不只是她,精神障礙者們也持續在努力的路上。一直到現在,低潮還是會襲來,郝天行笑說,自己還是常常焦慮,但當症狀出現時,朋友會先發現不對勁,知道該怎麼幫她,「以前我瘋起來的時後,會用比較激烈的方式,我的朋友都被我鬧過,很感謝他們還願意在身邊,可能就是拿平常的功德來換。」而王修梧則在一旁邊笑邊點頭,這大概是一種「很麻煩但又很有愛」的支持關係。
創傷可能不會好,它會蜇伏在生命裡,但你會學著怎麼面對它。
「你永遠不知道你 20 歲無法承擔的事情,30 歲有沒有能力了。」李昀同樣也持續努力對抗自己的低潮,今天好一點的時候,她可以站出來演講,為精神障礙者發聲,「我現在不用每天被藥物控制,不用再跟自己說我是一個病人。」不好的時候,她仍感覺自己處在一片荒原,眼見所見都是焦土,「我現在每天都會爆哭,因為過去 10 年都不會哭,人生很痛苦,但我情願清醒地痛苦。」
READr 關心您,再給自己一次機會:
自殺諮詢專線:1925(24小時)
生命線:1995
張老師專線:1980
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、精神虐待、性侵害、性騷擾,請立刻撥打110報案,再尋求113專線,求助專業社工人員。